|
一孩子正“方便”时闻后坑一声响屁,孩子回头望望,原来是挂牌子游街的“老右派分子”:“右派不许放屁!”孩子放大声音吼,老人低沉的嗓音朗朗回答了一声:“是!” 老人一向幽默,那年代又常常念叨这个“是!”,习惯了这个“是!”字,所以不知不觉地信口应了一声。 孩子一定是挺得意的,能和大人一样的发号施令了。他哪知道屁这东西其实是一股气,气集多了就会自然而然的泄露甚至爆发、爆炸,岂能听从什么人的命令,哪个“司令部”的命令都没有用,堵也堵不住,堵久了它的爆发力还会更强。有人说其爆发力的气压足足有几十公斤。不知这话是真是假,是民间的经验还是官方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又是怎样测量出来的。 人们为了考虑群众影响和保持自己的文明形象,遇上气憋得太足时,最上上策是躲起来,去一个僻静处释放。这位老人哪会料到,躲来如此的僻静处居然也让一小娃娃儿堵上了。 那日子许久以前,街头巷尾就有过孩子们的顺口溜:“屁、屁、屁,就是一股气,放不放,由不得你!不管谁的命令也都堵不回去,谁要堵,突然爆炸,吓着了你,还送你一身的臭气!”这个孩子在流行这个顺口溜时候年纪还要小,也许没有听过。 这是几十年前轰轰烈烈背景中的屁大的事,本来完全不必旧故事重说。想说是想到一个道理,对孩子要多给点爱的教育,情的教育,美的教育,要教育孩子关心老人、尊敬老人,要注意引导他们幼小的心灵,不要污染他们。 为什么要污染他们天真可爱而淳朴的心灵呢,为什么要在他们身上绷上一根仇视憎恨的阶级斗争的弦呢? 孩子对老人说的那话当然不是什么人教的,但他们天天看到斗这个又批那个,凶这个又骂那个人,天长日久的耳濡目染、近墨者黑,于是不知不觉就在大染缸里染了一身“黑”或者一身“红”,也学着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所以才说出了那样有悖于天理人情的话来。 “斗争的哲学”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好阶级斗争的纲,纲举目张”时代早已经过去,然而在如此春光明媚、万里无云的日子里,照样有人手把手地教着孩子,要他们表那个态、签这个名,反对这个、仇恨那个。何必如此“谆谆教导”,其实是教唆天真可爱的孩子呵。 孩子的年纪尚小,今后的日子长得很呵,历史尚在按照自身的规律变化和发展。今天这样对他们谆谆教导,待长大后若不再是那么回事,岂不在孩子们脑海里抹下一块阴影和疤痕。 比如有个孩子才念二年级,老师竟然也要她写诗“反击右倾翻案风”。七岁的孩子哪懂什么叫做“右倾翻案风”,连成人也大多是莫名其妙、稀里糊涂、人云亦云,天天跟着念“顺口溜”而已。 老师布置的作业非完成不可,要不然就没有分数,于是孩子也和成人一样人云亦云的写道:“我们红小兵,人小志气坚。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倒* * *”。后来的情况果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哪一天另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再来,追究起责任来咋办?何苦让小小的心灵担当起老“布尔什维克”们的伟任呢? 别继续这样对孩子进行这样的教育吧,若是年年月月、日日时时这般的栽培、洒水,苗子长成大树以后,会不会哪天把屋顶也顶塌的。 离开孩子说几句当年亲身经历。参加农村社教运动那年,一次吃完中饭恰巧和工作队副队长走在一起。当他看见前面水塘边一老妇时,不知道他的哪一根神经突然启动,竟然向我提一个怪问题。他问我如果那老妇突然落入池塘我去不去救她? 我回答说:不会水,但我会呼喊别人来救她。他又说:这是假设的呢!他接着“教导”我,如果我会水,把那老人救上来以后发现竟是一个地主婆呢? 我不想回答,心里明白,知道他要说一些什么,肯定会说我会犯立场错误的。我借故往岔路去了,心知肚明,看见有人落水,决不可能先去调查清楚,其阶级成份是什么才去呼叫求救的。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之心”。看见有人落水着急是人的天然反应,救人是出于“不忍之心”,哪里能时时刻刻都绷紧那根阶级斗争的弦。我什么也不想说,不再和他同道,从岔路一走了之。 天哪!如果广大农村全让这样的人去搞“教育运动”,去主持宣传工作,谁知道他们会把人家一个个教育成什么样子的人,会在农村搞什么样的教育,会把农村“运动”成个什么样? 再又想,倘若孩子们都交给这样的人去调教,后果也许不仅仅是“右派不准放屁”,或者还训斥别人“右派不许吃饭”,孩子也许会琢磨:都该消灭的敌人吃什么饭,岂不是浪费糟蹋粮食。长大成人以后就更不知道会有什么惊人之举。 有些年代是需要这种人的,一定会是一员天不怕地不怕的阶级斗争猛将,和谐社会可是不需要这样的人才。 借个古代笑话添趣:县官正审案,有人放了个屁。县官大怒,命三日内捉拿扰乱公堂的主犯。 哪去捉屁啊?狱吏只得将一纸包,里面包着那脏兮兮的“阶级敌人”呈上公堂,对县官说:“禀大人,主犯已逃走,只拿得他的家属随从在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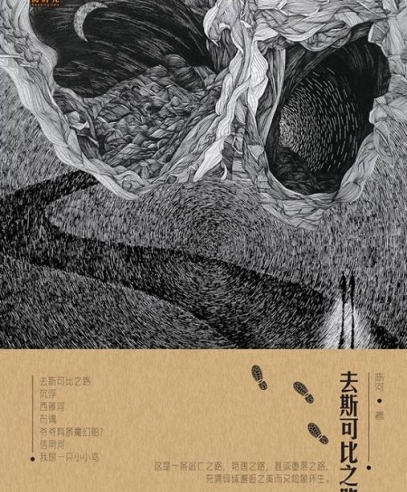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