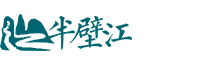|
手患了冻疮,疙疙瘩瘩的,暖和一些就奇痒。据说用芝麻花搓洗可以根治,我散步时留意了下,满田野斑斓着蚕豆花、玉米花、棉花花……可就是遍寻不着芝麻花。
电话中无意提起,随便问久已不侍弄庄稼的母亲:“田地里怎么没有芝麻?”妈说:“现在谁还种芝麻呀,不当吃不当喝,收成又少,白搭了几分好地。”妈奇怪:“怎么想起问芝麻?想吃了?”我随口说了手患冻疮的事,也说了用芝麻花洗就可根除的偏方。
次年夏,母亲一遍遍催我回去,最后居然限期在某日之前再不回家以后就别回去了。我在她一遍遍“回去回去”的督促中坐车换车辗转了大半天才见到她小麦色的笑脸。她连凳子也没让我坐,扯过我就走,趟过村庄,绕过小河,把我领到一片花地前,那一刻我呆了:全是花啊!洁白的花,芝麻花!
母亲左手牵起衣襟往上一提就拢成了一个兜,另一只手采下一朵朵芝麻花,我傻愣着:“妈,你做什么?”她说:“你不是手有冻疮吗?不是用芝麻花洗可以治好吗?你洗啊!”我说:“只是偏方而已,不知道管不管用?”她说:“不洗怎么知道管不管用,只有洗了才知道!”
我洗了。正是盛夏,手光洁得看不出任何冻疮痕迹,我还是蹲下身、垂下头轻轻地擦洗,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奢侈最美好最感动最难忘最小心翼翼最温暖的一次洗手,朵朵洁白的芝麻花,把我的手覆盖、包裹、呵护、揉搓。母亲采了一兜,又采了一兜,全部覆在我的手上,然后把我的手握进她的手心一遍一遍地揉搓,我看到母亲的手全是晒斑。
邻里告诉我,母亲为治我的冻疮,硬向别人讨了二分地,她只说一句话:“闺女的手冻了,只有芝麻花才能洗好啊。”她向人家承诺:她翻地,她下种,她侍弄,她只要芝麻花,收的芝麻全归人家。
入冬后,母亲隔两天就打次电话,回访疗效。我答:“还没冻哩。”她说:“天还没正经冷。”过了两天,不等天“正经冷”起来又打电话探情况,我翻来覆去瞅自己的手,郑重其事汇报:“还没冻。”她叮咛:“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等正经冷起来,她又说:“等到冷透才能知道效果的。”
冬天就这样在她的引领下过去,风暖起来,手真的没有再冻。母亲欣喜若狂,见人就说:“芝麻花真管用。”那一年,我还吃到了芝麻盐和芝麻酱(人家并没收下她的芝麻),芝麻炒熟后,原来那么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