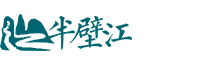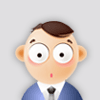|
11
我走了大约八百米,看到了另一条横着的路。它好像宽一些,我站在路口上等了十多分钟。
天气已经开始渐渐热上来,阳光的作用已变成先把地面上的一切晒干,再把干燥的一切晒焦。沙漠里没有风,但是有一种特有的热浪一样的气息。十几分钟以后,我开始失去了耐心。一个人沿着大路慢慢朝城里的方向走。
听到身后远远地有人按喇叭的时候,我转过身来,一辆破旧的白色加长大众车东倒西歪、七扭八扭地开到我身边停下来。我想,还真是象人们所说的那样。
这时候出现了最让人吃惊的事情:透过没有玻璃的车窗,我看到车子里挤了几个——中国人?!
他们的表情比我还要吃惊,好像大白天撞上了鬼一般。
“你是——?中国人——?中——国——人——?”开车的那个过了一会儿缓过劲来,有些激动地比比划划地用中国话问我。好像又不敢确定,故意把声调拖长,以为这样“外国人”也能懂。
我忽然灵机一动,想弄个玩笑开心。我用手指指自己,点头哈腰,很认真地用我大学时学的日语确定了自己想要的身份:
“日本人——,日本人——。”
“噢——!”他们先迟疑了一下,过了一会儿琢磨懂了,先后回过神来。
一个哥们已经被挤到后座,他们滕出个前排的位置让我坐上去。
“日本人,原来是个日本人……”车里前后座的几个中国小伙子兴奋地纷纷议论。
我忍住笑,一板正经地坐在那里。
“是不是来旅游的,问问她是不是来旅游的。”
“你问人家,人家能听懂吗?”
“用英语问,正好有个机会练练汇话,你不是整天学着吗?”
“这不好,这不好。咱那点口语,对人家外宾讲,影响不好。又是单身一个女的。”
“别让他讲,他那点英语,这不是有损国格嘛……”
还是问了,用英语:“you——,tourist?Tourist——?”
“Yes,yes。”我马上点着头,将手指握在胸前,用头点着他们问:“you——tourist?”
“No,No。”车里一片此起彼伏的No的声音,看来这个词所有人都会。
接着他们相互商量:
“怎么说,工地怎么说?”
“你告诉她我们是在这搞建筑的。”
“这太复杂,谁会说。”
一个出面用手比划,先指指他们大家,接着平伸了两只手掌,一层一层向上,最后比划了一个高高的长方形。
“啊,building。”我弄明白了。
有两三个人想起来,“对,对,building。”
“援建,盖楼怎么说。”
“不用说了,人家已经明白了。”
接着又有一个跟我比划,用手点了点眼下,“threeyears。”又用手掌比划前面,“oneyear。”
原来这援建也象上大学一样,四年本科。
后排座位上,他们在用不同省市的口音毫无顾忌地议论纷纷:
“真是,真吓了我一跳,跟你说吧,天天看的全是黑人,忽然冒出个不黑的——”
“我远远瞅着那两条腿就不对,咋裙子下边露出两条白腿来呢。”
“哎,你还说呢,我刚才正迷糊着,猛一睁眼,眼前个女的,不以为做梦见到仙女,还以为回到咱河北老家呢。”
这位跟我还真沾半个老乡。俺家的祖上出自河北胜芳,就在白洋淀的边上。因为靠水,人说是北方的江南。有水就养人,古时宫里选宫女太监的地方,因为人坯子好。我记得小时候看大姑的照片,瘦高的个子,穿着长及小腿的大衣,鹅蛋脸,头上系着丝围巾,眯着眼笑,风华绝代的样子,一手牵着一个很小的小男孩,那是父亲……
“他就是想女人想糊涂了。哈,哈哈哈……”
“别胡说你,啥影响,让人听去,还有纪律没。”
“女人倒没啥,想想也就过去了。其实这人出门在外最惦记的,还是家里那孩子。”
听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另一次在非洲的另一个地方,好像是在肯尼亚,听到过的一个当地人讲的笑话。七十年代的时候,有几千中国工人在他们的国家和附近的几个国家帮助修建公路和铁路,时间大概前后加起来有四五年。那些公路和铁路至今还在使用中,而且经过多年的雨季和旱季,一直保持了很好的质量。但是中国人最让当地人感到惊奇的并不是这种“人定胜天”的精神,而是成千上万的中国援建工人在那么热的地方工作了好几年,他们走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个孩子留下来。
当然这笑话是不能讲给他们听的,我自己也只好忍住不笑。
车子进城的时候,昨天夜里看不清的景物,在大白天里一目了然,是个很小但是很美的地方。市里不过一眼就能望到的几条街,却是花园洋房,绿树红花,和谐安详。如果没来过,是想象不出,非洲一个偏远的国家里,也会有这样的地方。
他们将车停在市中心小方场的旁边。小方场上种满了各种热带植物,绿树成荫。开车的中国小伙子指着街对面爬蔓花丛中的一扇门窗,我看到了一个大大的Information的i字。
我跳下车,和车里的人相互挥着手,朝街对面走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