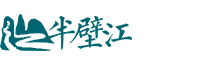|
4
他们停了一辆崭新的黑亮三菱越野车在门前。我根本没注意到这两个小男孩一样的年轻人,开着这么巨大的一辆车。
“是我哥哥的。”眼镜说。这让我想到他哥哥应该是个什么有权势地位的人,我想当地人里能有这种车的人应该不多。
两三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开始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来回绕,市中心有几条街上是有路灯的,但我仍然看不清路边的建筑和景物。那哥俩好像也不是很清楚的样子,一边开来绕去地乱转,一边商量着。
“不用担心,我们会找着的。”他们安慰我。
我们先是在一处路边停下,路边的平房是白色的,所以容易看清,一尺高的围墙做成一种装饰性的花边的样子,有着很优美的起伏。圆脸的男孩下车,一脚跨过围墙,趟过草地,在房前按门铃。我听到门铃响了好几声,但是没有人回应。我们又等了一会儿,圆脸的男孩跑上来,车子倒车拐过街角,应该是房子的另一个门廊,圆脸再一次下车去按门铃,还是没有回音。
车子又穿过了两三条街,这次停的街上没有路灯。圆脸男孩在一扇大门前按铃。门和院墙都高高的,有花树藤蔓的巨大阴影在黑暗中从高处压下来。过了一会儿,对讲器响了,圆脸男孩和对讲器里相互对讲了几句话,他又跑回来,说:“不行,他们说没有特殊情况是不对外的。”
“这里是教会的接待处。”眼镜告诉我。
车子又开始在几条街上慢慢地空转。
“这么晚了,去按人家的门铃,是不大好的事。”他们告诉我。
5
“你要在这里呆多久?”眼镜问我。
“现在不知道,我要明早在城里转转看再决定。”我说。
“如果住处离市中心远一些,你会介意吗?”他问我。
“噢,那没有关系。”
“你知道,这里没有出租车,也没有公共交通。如果住处离市中心远,你每天进城,都得走很长时间的路。”
“多走点路没什么。”我告诉他。
“你也可以搭车。”圆脸说,“不过如果有车看到你,他们也会停下来问你。这里都是这样的,不用害怕。这里没有犯罪率,并不象在外面传说的,或者在美国那样,一半的黑人都是罪犯。”
我笑了起来。接着我们一起笑了起来。
“你们知道,很好玩的事情是,就像人们知道你是中国人,就问你知道不知道李小龙,知道了李小龙,就问你会不会中国功夫……,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的……”
“真的?”
“真的。”
“话说回来,你到底会不会中国功夫呢?”
“会一点,应该不会比你们多……”他们俩笑起来。
其实,我就是坚持说我会中国功夫,又能提防得了什么呢。
6
“我住的附近,有一所国际学校,他们那里正在办一个什么暑期活动。这个学校有招待所,是可以住的,就是离城远些。”眼镜说。他一直在驾车,我坐在他旁边的位置上,圆脸在我们的后面。
“有多远呢?”我侧脸问他。
“嗯,离城大约有六七公里、七八公里。”他说。
“要过铁路,是在另一个方向。”圆脸说,他忘记了我在这里是根本辨不清东西南北的。
车子慢慢向另一个方向开去。很快就不再是柏油路了,四周又是一片漆黑。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眼镜问我。
“我是写小说的。”
他们俩笑起来,“你说的口气就好像你是烤面包的或换轮胎的一样。”
“就是,其实是一回事。”
“你写什么样的小说,史蒂芬·金吗?”
“哈,哈哈哈……”我们不约而同地奇形怪状地笑起来,这黑沉沉静寂无人的黑夜,两个黑人男人和一个浅肤色的女人……
“对,你应该写篇小说,写我们如何把你骗到车里,如何劫持你的故事。”那哥俩越发奇奇怪怪地笑起来。
“这不好,这种故事太简单。畅销书里的起伏情节总是过于廉价。我写的小说,对读者要求很高,他们得从轻描淡写的故事中读出在平淡下面比深刻沉重还要更有意义的质地来。就像复活节藏的蛋一样,蛋我是埋下了,你能找出来多少全看你自己的感觉和悟性;也象海上漂浮的冰山,水面下潜藏的比浮在水面上一眼能看到的要多得多。”
“哇——!”一个说。
另一个不买账:“我跟你说,她恐怕是因为自己不大能写出个究竟来,所以才想起来往读者身上推。”
我们又一同嘻嘻嘻嘿嘿嘿地笑起来。
你是不是听说过
从前有一个唐先生
他挑了风车一辆又一辆
他老人家真是战无不胜
圆脸大声唱起来,当我听清了他的唱词,不由得大笑起来。
“你也知道唐先生吧,喏,就是那个西班牙的骑士——?”他们两个也开心地笑着,“你们中国有唐先生吗?”
“呵,唐先生,我们中国的唐先生,可是另外一个,他不是个骑士,他是个和尚,他没本事单挑,只好结帮成伙地拉徒弟陪他到西方去取经。”
圆脸和眼镜又共同打着拍子,用原调又唱了一遍,只是临时换了歌词:
中国有个唐先生
他到西方去取经
“噢——!”我们三个齐声怪叫了一声,作为歌词的结束。因为车过铁路的时候,忽然都被死命地颠高了一下,头几乎撞到车顶。
7
另一片居民区里,黑暗中有一两点星星的灯光。路是沙石路,但是路边开始出现了路灯。
眼镜放慢了车速,“那是我的房子。”他向我指着路边的一幢小房子,房子立在中间,四周围着一米高的栏杆,小院落里好像种着一棵树。
“我明天一大早有事情要办,不然你明早可以来找我,搭车进城。学校就在前面。”
车子停在一个大铁栅栏门前,圆脸又跑下去按门铃,对着对讲机说话。之后门开了,我们开车进去。
校园好像很大,车子转来转去好一阵,停在了一幢很小的房子前面。
“是值班人住的地方。”眼镜对我说。
这次我们三个人一起下了车,眼镜按了门铃,“她怀孕了,是个孕妇。”眼镜用手在自己腹前比划了一个圆形。
“不是这个月,就是下个月了。是吧?”他问圆脸。
“应该是下个月,”圆脸说,“我们又要添丁进口了。”
“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问。
“不知道。在我们这里,都不提前去医院作B超,人们说对胎儿不好;再说,是男是女不能预料的惊奇,是上帝给人们最大的惊喜之一,是吧?”
我们低声说着,门开了,一个穿着长睡衣的妇女走了出来,“呵,都这么晚了,”她打着哈欠,腹前挺着一个很大的圆球,腰身有些笨重。
“等一下,”她又转身回到屋里,一会儿出来,身上已经又多披了一件外衣,“这夜里还是挺冷的啊,”她又打了一个哈欠,接着用手抚摸着高高隆起的腹部,“作孕妇就是爱睡觉,月份越高越爱犯困。”她自顾自地说着。
“就是你一个人吗?”她看看我。
圆脸已经从车上将我的手提袋拎了下来。
她转过脸和眼镜用当地话商量了几句什么。
眼镜对我说:“你介意不介意多交一点钱?他们这里没有单人房间,双人房间是两个床位,尽管你一个人住,但他们得开这个房间,所以另一个床位的钱也得交。”
“多少钱?”我问。
眼镜又问那个孕妇,接着告诉我,“是六十块钱,单人床位是三十五块钱,但是她说你得交双份。”
那孕妇望着我,耸耸肩,“这是上面的规定,我也没有办法。”她说。
我说我不介意,加在一起也并没有多少钱。
她收下钱,回屋去拿钥匙的时候,那两个男孩子和我握手告别,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重要的是你平平安安的。”眼镜说,“其实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也可以住到我那里去,就是我家里太乱了,再说我明天很早就要出去。”
我连忙止住他,我想今夜我已经很给他们添麻烦了。
“这没有什么,你一点都不用介意。”圆脸说。
我告别了他们,跟在孕妇管理员的身后,向招待所走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