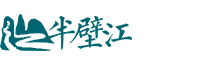|
大约过了一年蹭宗才缓过劲来。又像从前那样四处蹭吃、蹭喝、翻腾哥儿们的好烟、好酒、好茶,逮谁蹭谁的那股子烦人劲又上来了。 这天周末,蹭宗给几个哥儿们打电话。说老尹新开了家大酒店,找来不少小姐,不但坐台还出台,他做东请大伙儿热闹热闹。起初谁也没理他的茬,都知道他又在那设套儿。老范灵机一动,对哥儿几个说:“那小子整天想方设法地‘蹭’咱们,今天何不‘蹭’他一把?”韩先生说:“对!他不就好中途溜之乎也吗,今天咱也给他玩一把。” 大酒店座落在三零一国道边儿,主人别出心裁的在湖中建了几处水上餐厅。客人点完菜便乘小船来到湖中就餐。正值夏季,水上微风拂面,青萍涟漪。面对湖光秀色,美酒佳肴,老范、韩先生一边喝酒,一边夸赞蹭宗会办事。老范说:“这才是湖水煮活鱼呢,味道就是鲜亮!”韩先生说“这样的好去处花多少钱都值!还是蹭宗会办事儿。”蹭宗闻听更来劲了,对韩先生道:“这才哪儿到哪呀,看哥儿们下道菜,那才是色香味俱全呢。”老范知道他指的什么,便对他说道:“那还等啥呀,赶紧让大伙儿品尝吧。”蹭宗道:“你们先喝着,我现在就过去安排。”说着,起身登上小船返回大酒店。老范、韩先生几个看蹭宗离去,立刻叫了只小船钻进了芦苇荡。几个人一边打着酒隔,一边开心地等着看蹭宗的笑话。 蹭宗走进歌厅,对老尹小老婆说要小姐,那女人立刻招呼十几个小姐站成一排任他挑选。蹭宗背着手、挺着胸,神气实足地来回走几趟,不是说这个胖的象猪,就是那个瘦的象猴。摸摸人家的胸脯问是不是假的,拉拉人家的手,阴损地埋汰人家:“是不是刚放下锄杠就来了?”挑三拣四的好不容易选了几个送上小船,划到水上餐厅一看,禁不住开口大骂:“他妈的,这几个王八犊子,这么一会儿功夫全都穿了兔子鞋!” 平心而论,蹭宗道不是贪杯好色之徒,他就是喜欢打哈凑趣那种场面。这段时间大家都各忙个的,没时间、也没机会聚到一块。他闲着难受,就想整点事儿。弄个白吃白喝白玩,然后乘机溜掉。哪成想偷鸡不成蚀把米,反倒让人家给算计了。心里窝囊且不说,还被眼前这个主给讹上了。那个叫翠翠的小姐一看空跑了一趟,说啥也不让他走。说:“俺们不能跟着你白跑一趟,咋也得给点小费呀。”蹭宗说:“我他妈也没碰你要什么小费!”“怎么没碰,你拉我手了!”蹭宗自觉理亏,也觉得眼前这个主是个茬子。便想给她俩个钱儿打发了算了。于是便问:“拉你一下手要多少钱?”“二十!”“那就给你二十!”“那不行,你还摸我胸了呢。”“摸胸要多少钱!”“八十!”蹭宗一听要八十,立刻急了。骂骂咧咧地说:“全套下来才二百,这还没干呢,你就要一百,那还不如干呢。”那个小姐更不是东西,毫不示弱地说道:“谁不让你干了,一百元,让你干一百下。”“一块钱一下?”“成交”!”蹭宗这个气呀,混了这么多年社会,从来都是只占便宜不吃亏,今儿个一连气地栽跟头。一气之下干就干!三下五除二脱衣上床,满腔怨恨化做利器,象头发疯的骆驼把那妞儿弄得是喊爹叫娘,高潮迭起。她大叫道:“爽呀,太棒了,哥,快呀,别停下!”蹭宗说:“我到数了。正好一百下。”“哥,别停下,继续!”“再干算谁的?”“算我的,你别停下。”干吧,有买有卖有价有数。这活儿哪儿找去,只有我蹭宗有这运气。真可谓淋漓尽致的一场大战,两个人累的是狗乏兔子喘。蹭宗一边擦着一身臭汗,一边道:“讲好了的一元一下,我数着呢,一共干了四百五十下,正好四百五十元。扣除我给你的一百元,再扣除摸手、摸胸的一百元,你还得付我二百五十元。”那小姐气喘吁吁地反驳道:“你听说过小姐还得给嫖客钱的吗?”蹭宗说:“好歹你也算个“职业女性,”怎么着也得讲点职业道德吧。刚才不是你说的‘再干算你的吗’”“咱俩处‘老铁’,算你白玩行不?”“不行!给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蹭宗也不是真想朝她要钱,小母狗眼儿一转想出个主意,他说:“这样吧,你帮我办件事。”“啥事?”“过两天我领一个哥们来,你和他办完事儿把安全套封好,装在保温杯里悄悄给我。”“你要那破玩艺干啥?”“这你就别问。”“白帮你,不干。”“给你五块钱。”“五十!”“十块!”“一百!”“成交!” 自打那天起,蹭宗便开始琢磨一件事儿——蹭个种儿。老范?不行!长的太难看。林子?也不行,那小子太坏。还是韩先生,人长的帅气,学问也好。对,就韩先生了。劝人学好难,拉朋友干点小坏事还不容易。经不住几撺掇,两个人便鬼鬼祟祟地溜进老尹的大酒店。不一会,那小姐拿着蹭宗事先准备的保温杯出来,说:“东西给你搞定了,钱呢?”“他给你。”“他给我多少?”“你平时出台二百,今天我告诉他给你三百。”“缺德带冒烟,真损!” 蹭宗顾不上听她骂了,捧着保温杯开车就往家里跑。 蹭宗老婆怀上了。转年真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把个蹭宗高兴的天天唱着小曲儿洗尿片,跳着舞步热牛奶。把娘儿俩伺候的两头小肥猪似的。蹭宗心满意足地望着这娘儿俩,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蹭宗的日子可谓提前进入了小康。老婆一边带孩子一边经营着花圈寿衣店,自己当阴阳先生外带白事主持。每年少说也得收入个十万、八万。可那凡事都想着“蹭”的毛病依然如故。“蹭”朋友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心魔。 这天,开了五、六年的车需要换只轮胎。蹭宗跑到老范的固定供货商马二哨子的轮胎商店。一只轮胎从四百五讲到二百。蹭宗还觉得不满意,非让再搭盒烟不可。常言道:“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马二哨子做了十几年的轮胎生意,质量好的、次的,真的、仿的是样样俱全。看他把价压的这么低,便给他装上一只翻新胎。临到付款时,蹭宗大大乎乎地说:“记到老范账上吧!”马二哨子犹豫一下,说:“这样不太好,还是给老范打个电话,不然我也不好办。”蹭宗掏出手机,腆着脸理直气壮地说:“哥儿们,我在马二哨子这儿拿了一只轮胎,记到你账上了。开始他要四百五,我讲到二百。给你省下二百五。”老范随口骂了句:“我看你才二百五!”似乎也在忙,便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蹭宗去殡仪馆主持一桩葬礼,也是贪点儿床,起得稍晚了点。眼看就要来不及了,不由得加快车速度赶时间。快到殡仪馆时遇着个急转弯,他心里着急,动作不怎么利索,前轮碰到马路牙子上。只听“嘭”的一声,那只新换的前胎爆了。车子叽里咕噜地连翻三圈,蹭宗也跟着昏了过去。 蹭宗在医院抢救了两天两宿,伤势越来越重。腹中的几个主要器官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人眼看就不行了。见此情景,他老婆把老范、林子、韩先生等几个哥们儿叫来,想商量商量后事。大家心情都很难过,怎么说也是十几年的兄弟了,说走就要走了,能不难过吗。老范见他稍有点儿清醒,便坐在床边,拉着他的手说:“兄弟,我们哥儿几个都来了,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蹭宗淡淡地笑了笑,说:“我知道哥儿几个是来给我安排后事的,人到了这一步也没啥想不开的。”长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唉!我怕是过不去今天了。咱哥们儿好一场,我这一死你们准得给我随个份子。不如趁现在我还能看到,你们就给了吧。好让知道你们的情份有多重。”本来大家都挺悲痛的,让他这一说,把几个人弄得哭笑不得。气得老范问他:“你啥时候死呀?我们随了份子你再不死呢?”蹭宗说:“哥儿们,我今晚子时前必须上路!”林子说:“看这样子你好像急着死?”蹭宗又长叹一声道:“唉!怎么说我也当了一辈子阴阳先生,好歹也算个阳阴两界人,多少知道那边的事。好在今晚子时去的这拨儿都是有头、有脸、有权、有势的,在阳间时就把阴间的事打点好了,去了马上投胎转世。说是和美国交流,相当于公派出国,这不又让我给‘蹭’上了。”几个不了解他的同室病友,都以为他是伤重的失去理智在说胡话。只有老范等几个被他“蹭”一辈子朋友知道,他这爱“蹭”的毛病怕是至死也改不掉了。蹭宗喘息了一会儿,继续对老范说:“哥们儿,兄弟我‘蹭’了你一辈子,今天算是蹭到头了。我死后招待大伙的这顿饭,你可一定给我办的风光点儿。这可是兄弟我最后‘蹭’你一回了。” 唉!真拿他没辙!活着“蹭”了一辈子,死了还惦记着“蹭。”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老范只有应的份,还能说什么?蹭宗安祥地看着大伙儿,那张葵花脸上依然带着微笑,只是笑的有些僵硬。他慢慢地合上眼睛,显得很疲倦,呼吸越来越不均匀。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室内很静,静得让人窒息。看他以这样的方式对待死亡,大家心中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苍凉感。唉!这人那……。突然,蹭宗猛然睁开眼睛,俩手急切地在身上摸索。发散的瞳孔直逼韩先生。韩先生急忙走上前拉着他的手,轻声问道:“兄弟,你还有话要说?”蹭宗把手中的一张银行卡塞给韩先生,拉过他胖儿子的手放在韩先生手上,断断续地说:“这孩子今年才十一呀!是你的种儿,千万把他培养成人。银行卡的密码你知道,你IQ高......。 蹭宗死了。林子给他写的墓碑。正中大书:“祖宗之墓。”边儿上写着:“祖宗,生于一九六四年,卒于二零零六年。享年四十二岁。写完林子骂道:“妈的,死了还得叫你一声‘祖宗!’” 蹭宗死了一年,韩先生烦恼了一年。平白无故蹦出个儿子,这都哪儿跟哪呀。还有那张银行卡,愣说密码他知道,可他一点印象也没有。多高的IQ值能猜出死人的意思。走了还来个临终托孤,这年头培养一个孩子得多少钱呀。或许这张卡是他毕生积蓄?可不知道密码等于是张废纸。唉,真愁人!韩先生把他的生日、手机号、车牌号等凡是能想到的反复试了无数次,可没一个对的。直到有一天,韩先生上网聊天,遇到一个已经多年没说话的聊友。尽管脑海中已经没啥印象,可人家打招呼也不能不回呀。刚搭话那人便问:“这是你的QQ还是你朋友的?”韩先生一愣神,猛然想到:“我的妈呀,那死鬼经常用过我的QQ号上网,银行卡用的一定是我QQ的密码!” 韩先生急忙找个自动取款机,输入77889900。屏幕上显示:“密码输入正确!本卡存款余额人民币壹元整。” 气得韩先生“嘎”一声,抽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