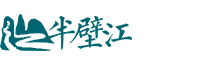|
原来,徐瑞祥从四清组调回来之后,一切通信往来都在监视之中。 听着这一堆刺耳的话语,徐瑞祥气得脸青一阵紫一阵,也不知他哪来的勇气,蹭的一声站起来,毫不服气地说:“连毛主席都说过,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怎么就不能给她谈恋爱呢?” 张开斌怎么也没有想到徐瑞祥敢给自己当面顶撞,气得直哆嗦,他当即自个作出决定:对徐瑞祥开除留用,每月发8块钱的生活费,负责打扫公社大院的厕所和卫生,出公社大院必须请假,视其表现,一年后再作处理。 徐瑞祥一下子被砸趴下了。 从徐瑞祥犯错误的身上,张开斌深刻地体到了“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的他老人家论断的英明。为彻底切断后路肃清余毒,他又责成红星大队必须对地主分子邵长坤批倒斗臭。 批斗邵长坤的大会,根据公社的部署,如期举行。 邵长坤被批斗后,带着文斗的污言秽语和武斗的满身伤痕病倒了。 邵美荣心疼着父亲,牵挂着远方的他,忍受着白眼的刺疼和唾液的狂砸。她发疯似的呼天:苍天呀,我哪辈子得罪你了,你这样没黑没白的不饶我?她又跺着脚的恨地:大地呀,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一刻也不放过对我的惩罚?这到底是为什么?你们总是把冰凉的湿布往我滚热的身上披挂? 邵美荣也病倒了,吃什么吐什么,邵母担心着丈夫牵挂着女儿,理性告诉她,她必须坚强起来,不然这家人就完了。母亲给邵美荣买了感冒药和止呕吐的药,吃了都白搭,这可愁毁了邵母。一天她又在为女儿的病发愁时,也不知怎么的她竟把女儿的病与外边纷纷扬扬的闲话连上了,她不敢往下想,便试探着问女儿:“你那事几天了?” 邵美荣这才想到,自己的例假已经过了半个多月了。可转眼一想,哪能这么巧,就他临别那一回。可又过了几天,印证了母亲的判断。瞒着邵父,母女俩慌作一团。作掉吧,比死了都难,得大队开信,公社批准。自己又是这样的背景,谁给你开信,谁给你批准呢?更可怕的是,这事传到了公社里,徐瑞祥还不知要遭多大的罪呀。 情急之下邵母想出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趁着还没显出来,赶快嫁人吧。 邵美荣哭得天昏地暗,在万般无奈之下,依了母亲的想法。 邵母想:这将就的婚姻还能有什麽挑头,只要那边成分好就行了,免得日后再跟着受煎熬。 经人介绍,邵美荣做了填房,在20里外的朱集大队,男人叫朱茂田,比邵美荣大一旬,还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叫朱兰兰。 过门后七个月零三天,临产的阵痛促使邵美荣不得不编出瞎话:扛东西挵着了,可能要提前生产。婆婆吓得慌了手脚,丈夫急忙找来生产队的排车,拉起她就往公社医院里跑,还好,虽有些难产,还算顺当,又是一个千金,取名朱英英。朱茂田并不嫌弃,他只有一个想法,只要保住了大人的命,比什么都重要。他深知穷人家找媳妇的艰难啊。 从进产房的那一刻起,邵美荣的眼泪就没有干过,她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和其他女人一样,生产的时候孩子的亲生父亲也能陪伴在自己身旁。又是一阵的剧烈疼痛,她脑子里仿佛幻化出了徐瑞祥的身影,他叫她稳定情绪,叫她不要多想。听着他的话,她心里好受多了,呻吟中便有了自豪,嗔怪中也有了撒娇,生产的疼痛也由此减轻了不少。然而当她从幻化中走出来时,眼前的一切依然凄惨和悲凉。 孩子一天天长大,邵美荣在孩子身上一天天捕捉着徐瑞祥的身影,看着这苦涩的爱情结晶,她心里时而泛甜,时而泛酸,时而稳定,时而又烦躁不安。 开除留用的徐瑞祥,由于表现较好,更重要的是与邵美荣划清了界线,组织上认为他已经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便在一年后恢复了他的政籍。 其实,徐瑞祥哪天不在思念和牵挂着邵美荣呢?现实实在太残酷了,他不能想爱就爱想恨就恨呀,只能把这份感情深深的埋在心里。其间,得不到邵美荣的一点消息,他急得多次上火,嘴角上的泡消了又起,起了又消,一直就没有好过。恢复自由后,得知邵美荣已远嫁他人,并且又是那样有婚姻背景的男人,他难过的直捶头,精神到了崩溃的边沿,觉得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他想到了喝农药、割手腕等多种结束生命的办法,但他最怕这事办不彻底,半路上又被人再从死神那里拽回来,他并不怕落下残疾什么的,而精神就更难受了。那段日子他一直处在游离和不安中,黑夜和白昼的交替,对他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他觉得一切都没了灵性,风吞噬着他的时光,雨为他添加惆怅,就连十五的月亮与太阳的擦肩而过,他也会泛起感伤,他诅咒苍天,就是注定的分离,停留片刻诉诉衷肠又有何妨?他也常常看着鸟儿发呆,甚至突发奇想,人要是能和鸟儿一样该有多好啊,空中永远留不下飞翔的翅膀。 一段时间活着与死去的思想较量,徐瑞祥活着的勇气败给了死去的思想,就在他要拿定主意的那一刻,最疼爱他的奶奶肺癌晚期的病历报告单横在了他的眼前,浓浓的血脉亲情提醒他,为了奶奶,去那条路的脚步必须暂缓。 沉默渐渐成了徐瑞祥的习惯,但现在的时光依然打磨着他过去的岁月,但比先前平和多了。再有人给他提亲,他也没有那么烦躁了,只是不冷不热的应付着,从不给人家见面。父亲嚷母亲劝也都白搭。末了,还是奶奶的话管呼,为了却奶奶有生之年见到孙媳妇的愿望,徐瑞祥定亲了,女方是供销社站柜台的营业员刘贞兰。刘贞兰性格温柔善良,特别会体贴和照顾人,过门后,深得奶奶的喜爱和公婆的赞扬,徐瑞祥也开始慢慢接受着她。一年后,刘贞兰生了个小子,取名徐福来。这段时间,做人父为人夫的责任,占去了徐瑞祥不少的空闲时间,一有空他也知道往家里跑了,知冷知热地围着大人孩子转。 徐瑞祥的工作受到上上下下的好评,不仅领导放心群众满意,而且有几项还很有创新,成了县里推广的范本。不久他就被提升为分管农业的公社管委副主任。他问的事多了,责任大了,腿也更勤了,经常深入生产队的田间地头,查民情听民意。一天他又去了公社一个最偏远的大队,溽热的中午头,大部分生产队都提前收工回家避暑去了,路上几个零星走路的人,被太阳赶得匆匆地交替着脚步。他的车子被埋在玉米地的田间小路上,车里的空调不惜力的吹着,但司机小孙的脸上还是挂满了汗水。突然,前边出现了一个妇女,她背着一捆草,手里牵着羊,另一只手里还提着一只断袢的凉鞋,徐瑞祥这才发现,那女的竟光着一只脚走路。小孙并没有按响喇叭,那女人听到身后有车的声音,就拽着羊一个劲的往路边上靠,期间,牵羊女子一个不经意的转脸,使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徐瑞祥像触电一样抽搐了一下,把小孙吓了一跳:“徐主人路宽着来,你不用怕。”说着车子就超了过来,徐瑞祥赶忙叫停,小孙犯了疑惑,咱的车子已经过来了还停干什么?心虽这样想,但车子还是停下了。徐瑞祥急忙打开车门,下车的左腿慌慌的还被车门别了一下。 牵羊的女人吓得直往后退,心想:我已经躲开了,你们还找什么事?便往下拉了拉戴在头顶的草帽,以壮壮自己的胆子,平平自己的心态。 “你还好吗?”这温馨的问候虽有些发颤,但很耳熟,一种急切的心情促使邵美荣急忙抬起头,徐瑞祥正泪眼一双的看着她。啊,原来真是他,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他伸过手来握住她的手时,她才“哇”的一声哭了,像出门在外受了多日委屈的孩子见到久违的母亲一样,哭得没有一点顾忌。 徐瑞祥心疼的像当年一样,要去给她擦去脸上的泪水,下意识的瞅了司机小孙一眼,便把手缩了回来。 徐瑞祥关切的问着些别后话,邵美荣总是宽慰他:一切都很好,叫他放心叫他别牵挂。但他看着她那断袢的凉鞋,烂边的草帽,裤子上的补丁,还有眼里的忧郁,脸上的沧桑,心想,一切都摆在那里,你再说好听的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心像被掏出来拽到蒺藜窝里一样刺痛着。 徐瑞祥叫司机小孙把她的那捆草放在轿车后备箱里,让他先走,在村头等候。司机小孙不再纳闷,因为他看出了跳在一起的两颗心。 徐瑞祥和邵美荣像当年一样并肩走着,忧伤的脚步好像又踏出了当年的快乐,小山羊乖乖地跟在他俩身后,就像他们的女儿一样。邵美荣一阵的甜蜜,脑海里闪出了三口之家的幸福模样。她几次想提起女儿,可是几次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一丝凉风吹来,两个人都感到了多日没有过的凉爽。 早早来到村头的司机小孙,放下那捆草,耐心的等候着。 这段不算近的路程,邵美荣今天觉得近了许多,没大工夫就来到了村头。 要告别了,徐瑞祥站在车旁,脑子里空白一张,呆呆地看着她背草离去的身影,竟连一句告别话的都没有。 小孙礼貌地按响了告别的喇叭,而后一溜烟似的跑了。邵美荣的心好像被他带走了一样,空荡荡的站在那里,直到踮着脚尖也看不到车的影子为止。 打这之后,两颗心又活跃了起来。 邵美荣常常静坐在黑夜里,享受着思念在脑海里翻腾的惬意。百虫的四处鸣唱,深情的迷离月光,都会勾起她无边的遐想,她想过去,想现在,也想到了未来。但现实又会迅速的把她从梦幻中拽回来,她有夫,他也有妇呀。她埋怨命运的作弄,为什么这一生只能叫她俩在彼此的对岸中忍受折磨,独吞泪水呢?但转眼一想,她又是幸运的,因为有一颗疼爱她的心一直在牵挂着她。 (责任编辑:admin) |